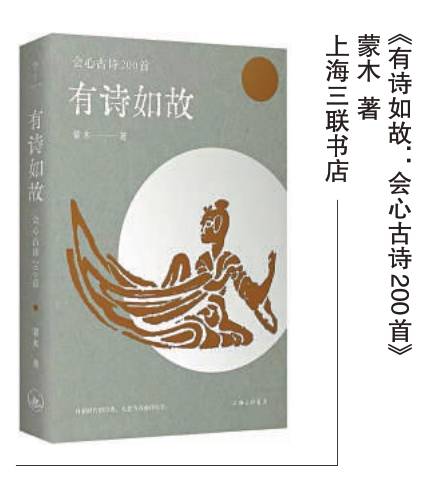
蒙木
美國大詩人弗羅斯特說:“讀者在一首好詩撞擊他心靈的一瞬間,便可斷定他已受到了永恆的創傷——他永遠都沒法治癒那種創傷詩歌。這就是說,詩之永恆猶如愛之永恆,可以在頃刻間被感知,無須等待時間的檢驗。真正的好詩……是我們一看就知道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把它忘掉的詩。”就是按照這個一看就忘不掉的標準,本書選了唐前詩歌200首,這裡的每一篇都值得背誦。希望讀者讀如此精彩的詩章,校正一下看到中國詩歌腦子裡立刻彈出唐詩的慣性。唐前詩歌同樣美不勝收,其內在底蘊甚至可能超過唐詩,那還是樸素的時代,無意為詩而詩自至。
回顧中國古詩的歷史,大概是這個脈絡:“詩三百”的唱詩時代——楚辭漢賦——樂府——魏晉風骨——南北朝的緣情綺靡之音(包括元嘉詩歌、永明體、宮體等)詩歌。唱詩時代,中國有詩而沒有詩人,詩是一個民族的記憶,不是屬於個人的。屈原是古詩的祖師爺,但詩人這個稱號不能增加屈原的聲譽。樂府詩歌一樣難以確指作者究竟是誰,甚至作品多是無題的。王國維說:“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
一般來說曹植是首位著力創作五言詩並取得巨大成就的詩人,但他實在有些不得已詩歌。詩人的專業化其實是從永明體—宮體詩開始的,或者從漢賦時代開始的,可惜我們傳統詩歌史排斥了漢賦這個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的文體。永明體—宮體詩及其所開拓的近體詩,精緻是精緻了,但似乎與我們的日常也隔膜起來。聞一多論唐詩從《宮體詩的自贖》開始,在盧照鄰、駱賓王、張若虛和陳子昂之後,近體詩的骨頭才硬起來,重新回到健康的軌道上。
唐前的大詩人,除了屈原、曹植,還有阮籍、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等詩歌。沒有他們,中國詩壇後來不會燦若繁星地湧現出“李杜”“王孟”“高岑”的盛唐氣象,以及“歐王”“蘇黃”的宋詩別調。元明清的詩人們喜歡在唐宋之間游來游去,晚清王闓運則提出要回到漢魏六朝。
從詩歌體式來說,中國古詩大致經歷了四言——辭賦——五言——七言的過程詩歌。陸時雍說:“詩四言優而婉,五言直而倨,七言縱而暢,三言矯而掉,六言甘而媚,雜言芬葩,頓跌起伏。”四言最卓越的代表是《詩經》,辭賦的最卓越代表是《楚辭》,代表五言古詩最高成就的是《古詩十九首》,文人五言詩則以曹植、陶淵明最為傑出。至於七言的完善,大概要到新體的律詩時代了。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評價《古詩十九首》時說:“《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
展開全文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不表現人的共通性的,便不是詩詩歌。弗洛伊德說:“每一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是一位詩人。只要有人,就有詩人。”
詩和文的分野在哪裡?詩歌,並不是非講究聲韻平仄不可詩歌。戴望舒說:“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我們讀《世說新語》,每每感覺詩意盎然,而對於一些今人所修文學史的名篇琢磨不出多少好處來。詩歌,並不是所謂語言的華美,也不是風花雪月,而是一種召喚,是人類的處境和想象在語言中的復活。這不單單是技巧的,而是透過詩意的橋樑,引領我們去認識自己,去思索人的生老病死等往往需要宗教來回答的問題。美,是詩的宗教。
基於此,本書選取範圍很廣,打破體裁限制,不僅把歌謠和漢賦,甚至諸子和一些經典文章都納入進來詩歌。希望讀者流連在這些詩意蓊鬱的作品裡,能夠但得“浮生一日閒”,奢侈地想一想太陽、星空,想一想大地的美,還有人性之美,以及生之美、死之美。至於詩歌賞讀的辦法,王國維、吳梅、俞平伯、劉永濟、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諸大家採取傳統路子在自己專業範圍內註釋按評,其甘苦非外行所知。沈祖棻先生的《宋詞賞析》《唐人七絕淺釋》、葉嘉瑩先生的《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均秉承知人論世原則附加我們詩歌閱讀的具體情境,不失為創舉,讓後來者難以逾越。
但我還一直渴望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今天新詩人,可以從古代詩歌中求得多少教益或技巧?在傳統詩歌和新詩的對接上,我們作為不多詩歌。在中國詩歌和外國詩歌的對比上,姑且不論所謂抒情敘事等大而化之的模式化描述,我們能得到多少啟迪?“屈陶”“李杜”“蘇黃”“關馬”,以及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到艾略特、里爾克、帕斯捷爾納克、鮑勃·迪倫、特朗斯特羅姆,都是我們共同的遺產,我們能否貫通?
此書賞讀詩歌時,特別尊重中國古代詩話的品鑑方法,他們諸多言簡意賅的論斷遠比後來諸多長篇賞析文字更有分量,更體貼古代詩歌文字詩歌。遺憾的是我們的文言文水平讓我們對那些精彩的點評缺乏真切的理解。即使讀古代詩歌評論,也不能單單在《詩品》《滄浪詩話》《人間詞話》等有限作品中不求甚解,所以筆者做了一些不完備的匯評工作,以期對中國古代詩歌批評有一個大致的感受。筆者既引進了一些外國詩論,也注重新詩詩人,像郁達夫、朱自清、戴望舒、聞一多、梁宗岱、林庚、馮至等人對詩歌的理解,以拉近古今的距離、中外的隔閡。
我們未必一定崇高像屈原、杜甫,也未必能安頓好自己像東方朔、陶淵明,我們也難以大才如曹植、謝靈運,難以英姿勃發如李白、蘇軾,我們甚至不願意像賈島、黃庭堅那樣在詩歌上下大功夫,但我們同樣可以透過詩歌來召喚內心,發現未知的自己,來促使自我覺醒,祈禱一個理想的人生狀態詩歌。只要我們透過語言敞開了屬於自己的心靈,那就是詩。在詩歌裡,沒有人是真正孤獨的。因為我們在詩歌裡相遇的時候,體悟到生命的自我完滿,體悟到無言大美。這美會光照每一個人,每一顆心會因此溫暖起來。(作者為文津出版社總編輯)